close
專訪《二十二》導演郭柯:讓“慰安婦”從歷史符號回歸為人
關鍵字: 中國“慰安婦”人數“慰安婦”電影《二十二》《三十二》日本慰安婦中國慰安婦幸存者慰安婦韋紹蘭
【被訪者/《三十二》、《二十二》導演郭柯,采訪/觀察者網 李泠】
1991年8月14日,時年67歲的金學順(Kim Hak-sun,1924-1997)作為第一位韓國證人,在公開場合召開記者會,向世人講述二戰時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的受害經歷。
26年後的今天,我國首部獲得公映許可的“慰安婦”題材紀錄電影《二十二》在多地影院正式公映。
《二十二》一名,取自於紀錄片拍攝時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幸存者人數。因那段沉重的歷史至今七十餘年,當年的受害者如今已是耄耋年紀,這一人數正急劇下降。
先前有調查統計,亞洲“慰安婦”數量達40萬,其中中國占20萬,考慮到部分老人不願提及往事等因素,實際數字可能在此之上。
2012年,郭柯導演拍攝完成相關紀錄短片《三十二》時,全國公開身份的幸存者人數已降至片名所提——32位。
剛過兩年,幸存老人再減10位。
至《二十二》公映前,當初拍攝的老人,在世的僅剩9位。
台灣商標查詢 從《三十二》到《二十二》,郭柯導演的紀錄似一場與時間賽跑的終極搶救,將70年前一群特殊的戰爭受害者從歷史廢墟中挖掘出來,挽留在世人眼前。
在世人的固有觀念裡,那些年的歷史,是殘酷悲烈的;回憶給老人帶來的傷痛,是沉重不堪的。而郭柯導演與她們接觸後,這一想象被顛覆——“走不出那段歷史的,不是‘慰安婦’,是我們自己”。
《二十二》公映前夕,觀察者網專訪該片導演郭柯,就《三十二》《二十二》臺前幕後、“慰安婦”的刻板印象與真實形象等聊談一二。
《三十二》:人生隻愁命短不愁窮
2012年,郭柯導演在微博上看到一篇名為《世界上唯一公開身份慰安婦:兒子至今未婚》的報道,講述瞭90歲的“慰安婦”韋紹蘭和她“鬼子孩子”的故事。因被這段歷史吸引,他投入數年,用電影形式將韋紹蘭老人的生活狀態完整記錄下來。
韋紹蘭老人(圖/郭柯導演提供)
“人生隻愁命短不愁窮”、“這世界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紀錄片《三十二》鏡頭下的韋紹蘭老人回憶當年與日軍相關的場景時會抹淚,但想起童年的友伴與歌謠,念到現在安平的日子,更多的是樂呵呵的笑容……
韋紹蘭老人:“人生隻愁命短不愁窮”(圖/豆瓣)
觀察者網:拍《三十二》前,有沒哪些設想好的拍攝方案?為什麼最後選瞭“適度的靠近,真誠的交流,靜靜的聆聽和深情的凝視”這麼一種紀錄方式?
郭柯導演:《三十二》可能沒那麼純粹,有一些不太合適的地方,如擺拍。那時剛接觸紀錄片,不太知道該怎麼拍,憑感覺做。擺拍,就是看畫面好,會請老人走一走。如開頭老人去政府領錢那一段落,畫面比較講究,是因為我們挑選好瞭的。但是,這其實有什麼意義呢?在幹嘛呢?表現自己對畫面的理解,告訴觀眾自己多有審美?這樣一來,把老人擺到哪兒去瞭?我覺得那時候的想法非常滑稽。
《二十二》和《三十二》隔瞭一年多,我學會瞭更加客觀地記錄。如看到老房子,不再覺得結構好看、想著怎麼拍。這是我們的習慣,但這些都不重要——我們要先把習慣拿掉,要先知道跟老人相處是一種什麼情感。
觀察者網:您曾表示,拍攝時自己的身份從“社會觀察者”進化為“傢人”。若是“傢人”,與“客觀地記錄”是否會沖突?
郭柯導演:不沖突。如果我奶奶有這方面的經歷,我也願意把它拍出來,但是,問問題一定要有尺度。你可以問她們,“日本人當年過來時在村裡是什麼樣的”、“有沒把你抓走”等,但要點到即止,她要不願意提及日本人怎麼強奸,就不要再問。如果是我奶奶,我一定不會問,我時刻把這身份作為設想。你想想,若看見一個導演在拍自己奶奶時問這些問題,是不是想上去踹他一腳?
郭柯導演與韋紹蘭老人(圖/郭柯導演提供)
觀察者網:社會普遍認為,“慰安婦”幸存者的個人經歷某種程度上反映瞭國傢那一時期的歷史面貌。在挖掘歷史深度與考慮老人情感兩者間,您選擇後者?
郭柯導演:對。我是一個自由職業者,不是體制內的,所以好像對這方面不太敏感。我從小是奶奶帶大的,跟老人在一起,就覺得應該多相處。至於“慰安婦”這頂帽子,我也接觸到社會上的一些信息,知道她們是怎樣的遭遇。但是跟她們相處以後,我覺得這方面不是太重要。
而且,說實話,還有一些私心。以前拍電影會想能否去挖掘一些更深的東西,但你可以回想自己看過的任何一部好電台灣商標註冊影,它都是有感情的。我們也在追求做出一部有感情的影片。在《三十二》、《二十二》中拍攝老人們的日常生活,就是情感表現。這種感情是出於對老人們的關懷,而不是作為歷史調查者去挖掘當初的歷史。
有觀點認為,她們背負著國傢歷史。其實是我們在讓她們背負著,她們天天過著平靜的生活,哪兒背負啊?走不出這段歷史的,是我們自己,不是老人。國傢公祭日,我們讓那些“慰安婦”站出來供國人銘記,那平時呢?除瞭公祭日知道那些人是“慰安婦”,還有人知道她們住哪兒嗎?還有人知道她們姓什麼嗎?還有人知道她們的傢人什麼樣嗎?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我就是想讓大傢在非公祭日的時候看看這些老人是什麼樣的生活狀態。
鄧玉民老人(圖/郭柯導演提供)
林愛蘭老人(圖/郭柯導演提供)
毛銀梅老人(圖/郭柯導演提供)
王志鳳、符美菊、李美金老人 (圖/郭柯導演提供)
觀察者網:您在兩部紀錄片中多處使用韋紹蘭老人唱的“人生隻愁命短不愁窮”,是認為歌詞最能真實反映她們現有的生活心態麼?
郭柯導演:對的。不管這歌是她自己的總結也好,是當地的民謠也好,從韋紹蘭老人嘴裡說出來會讓我們有更多的體會。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說出這樣的話,大傢會覺得沒什麼力量,但一個90多歲又經歷瞭這麼一段歷史的老人說出來,大傢會覺得她心態很好。從《三十二》用到《二十二》,就是要把她的這種態度延續下來,讓更多的人能看到、能聽到、能體會到。
觀察者網:央視先前報道上海“慰安婦”遺址海乃傢時曾提到,《三十二》在國外不少電影節上提名甚至拿獎,但報名國內電影節,總被拒之門外。您瞭解其中緣由麼?
郭柯導演:不好評價,可能是因為題材吧。大傢沒有真正關註和瞭解“慰安婦”這一群體,所以會覺得“慰安婦”是冷門題材。而且,我那種拍法也不都能讓人接受,他們可能會說“你憑什麼一點態度都沒有?”
電影節,很多時候要求導演要有自己的立場,對社會要有自己的看法。這太犀利瞭吧……對這題材,我若要有自己的看法,我是不是太狹隘瞭?我三十多歲,還在不停地接收社會給予我的信息,憑什麼對它有看法?在這題材上,我是不能有什麼看法的。我確實覺得自己就這麼幾兩重,沒資格對90多歲的老人形成自己的評判。
圖截自央視《新聞調查》之“一座慰安所的去與留”
說到海乃傢,你也看到小朋友對她們怎麼理解的。問題難道出在這些小朋友身上?問題在於我們怎麼傳播,錯在我們,不是他們。有一點,我們一定要看明確。拍“慰安婦”,如果還揪著日本、歷史不放,傳達給下一代的,就會缺少正面的東西,就會不去關註這些老人真實是怎麼樣的。
所以,我每次出席國際電影節時,一定會感謝他們,跟他們說“我真的沒有拍得很好,但感謝電影節的包容,因為你們的包容能讓你們國傢的民眾看到中國有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我不知道國內一些電影節為何不給這片子一個機會,多一點包容,讓我們去看一看這些老人。
《二十二》:讓“慰安婦”從歷史符號回歸為人
2014年1至7月,全劇組23位工作人員在經歷瞭11996公裡的跋涉、5733公裡的飛行、32海裡的輪渡、16所賓館的下榻、11種語言、9位當地人的翻譯後,在29個拍攝地(5省、13個市縣),對22位老人進行瞭拍攝。
分別在毛銀梅、韋紹蘭二老傢(台灣商標申請圖/郭柯導演提供)
成片無歷史畫面、無解說詞,音樂僅在片尾使用,“力求真實再現22位老人當下的生活與最為細膩的情感流露”。
拍攝之途艱辛勞頓,片子面世歷程也是一波三折。拍攝初始,投資人撤資,郭柯導演隻能向張歆藝求助100萬;完成制作後,宣發費用緊缺,靠29135位朋友眾籌,獲得100萬元;為讓片子登上熒屏,借鑒韓國同題材電影《鬼鄉/歸鄉》經驗,二次眾籌。
影片公映消息確定後,“毒舌電影”呼籲“能多讓一個中國人看到就多一個”,共青團中央也在微博號召“如果能找到排片的話,去看看吧”……
觀察者網:在拍攝這片時,您覺得最困難的是什麼?是搶時間拍攝老人們,是資金問題,還是其他?
郭柯導演:都不是。錢,張歆藝借瞭;團隊,更沒什麼問題,大傢拍那麼多戲,志同道合。說簡單點,給錢幹活,拍攝運作機械化操作,沒什麼可難的。
我覺得最困難的是,團隊該以什麼身份去面對她們,包括怎麼去提問,怎麼跟她們相處。真把她們符號化嗎?為挖掘歷史,費盡心思套她們話嗎?沒必要。最難的是放下這些東西,去肯定老人,去做一些看似非常無聊的東西。我們每天陪著她聊天,看看她掃地,去拍一些她的日常。對拍戲的來說,這些完全不可想象——這是在幹嘛呢?但是,我們就放下來瞭。
這是一個非常愉快的過程,大傢都沒什麼壓力,不要求今天要出什麼畫面。今天她幹什麼,我們拍什麼。她中午睡大覺,兩三個小時,我們也睡。現在拍戲,跟包工程似的,大傢拍完就散瞭。估計是大傢心中有這麼一個比較特殊的記憶,再加上這片子屬於“有意義的東西”,所以拍完兩三年,大傢一看到片子的消息,仍會自動轉發。
與駢煥英老人對話中(圖/郭柯導演提供)
觀察者網:《二十二》的眾籌文案裡寫著“讓這部飽含瞭我們心血與熱情的電影,面對殘酷的商業市場時能‘有尊嚴’地活著。”“有尊嚴”三字怎麼理解?
郭柯導演:哈哈,我能說這是宣傳團隊編輯的文案嗎?我也不太會說這種煽情的話,什麼“有尊嚴”地活著……這怎麼就沒“尊嚴”瞭?有時候沒辦法,大傢理解一下,因為現在是商業市場,得有一些相對契合市場的做法。
觀察者網:一位志願者跟您轉述,一位幸存者老人看到80多歲的日本人的照片後,笑瞭,說“日本人也老瞭,連胡子也沒瞭”。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當時“沉默瞭,增加更多的思考”。請問您還記得多瞭哪些思考嗎?
郭柯導演:就像剛才提及的,70年過去瞭,大傢都把“慰安婦”當成一個符號,以為她們被日本人傷害過,所以必然對日本仇恨。現在看到的新聞,不少也是老人死不瞑目,一定要讓日本人道歉。我們也認為這是“慰安婦”應該做的事情,認為這些是她們應有的狀態。但是,你真正接觸她們以後,會發現她們不是這樣的。70年是一個什麼概念?真正的老人如果天天背負著這樣的痛苦,她能活到90歲嗎?所以老人說出那句話時,我就感慨“人性啊,真的是這樣”。
觀察者網: 《二十二》末尾一年四季變換的鏡頭,是否有什麼寓意?
郭柯導演:我幾次站在這山頭的時候,內心有很多感慨,比如時間會慢慢流逝,也會改變很多事物,如這山頭,我們看不清楚瞭。其實,同一個鏡頭,不同的人看,意思有很多。這感慨,是出於我個人的經歷,相信會讓大傢產生共鳴,但這共鳴不一定是一條線上的。大傢有各自的生活經歷,理解角度不一樣,但相信鏡頭會和他們的過往經歷產生一些化學作用。
關於“慰安婦”的虛與實
觀察者網:截至8月8日,《三十二》豆瓣評分9.2,《二十二》評分7.9?您如何看待這分數差距?
郭柯導演:很正常。《三十二》中韋紹蘭老人的人生經歷坎坷些,戲劇沖突強一點。她不隻是“慰安婦”制度的受害者,還生下瞭日本人的孩子,這些可看度強些,再加上她又那麼樂觀,反差特別大。另外,情節走向在觀眾心中是波浪形的,觀眾情緒剛下來,看到(韋紹蘭)生瞭日本人的孩子,又被吊起來,再知道這日本孩子遭遇,心情掉下來,當看到韋紹蘭老人回憶快樂的童年部分,“咻”地又拔高。大傢看《三十二》時心情起伏很大,所以它的評分會高。
《二十二》中,老人們是平靜的、內向的。把它做得熱鬧,配些以前的畫面資料調動觀眾的情緒,我覺得這是一種特別不尊重觀眾的方式。告訴你“你看這老人多麼可憐,當年日本人多麼可恨”,這是多麼幼稚的一個行為啊。但是,大傢好像都吃這套,喜歡讓我們(創作者)告知,而不是互動。
點映前,《二十二》在豆瓣上評分才6分,當時我會覺得“啊,怎麼會這樣”,那時《三十二》的評分是8.9,差距特別大。點映後,《二十二》的評分就慢慢漲起來瞭,到現在漲到7.9,我還是很欣慰的,說明有很多人能體會到這種情感。
豆瓣上《二十二》評分不斷上漲,截至8月14日,已漲至8.6分
觀察者網:一些看完《二十二》點映場的網友認為片子結構松散、節奏偏冗長、空鏡頭太多,這些是您有意而為之的嗎?
郭柯導演:我這是把我看到的東西帶給大傢。分佈在中國20多個地區的老人,我怎麼把她們結合在一起?難道非要劇情化,把她們弄成一個群體?在黑龍江有位老人,我就跟觀眾講黑龍江的老人現在是什麼樣的;湖北有一位老人,就說湖北的老人現在如何。講她們的故事,就是這麼生硬,這麼片段式。
我能想到的結合,就是拍一場雨。“你看,在這老人傢這裡,下瞭一場特別大的暴雨,誒,今天海南也下起瞭雨,李美金老人就住在那兒。”我唯獨能做的,就是用自然環境來銜接她們。
空鏡頭多,是因為去老人傢裡,我得或遠或近地看她——一直盯著她看,這多不禮貌啊。看一眼老人外,肯定得看看她的環境,看老人床上擺的東西,看老人傢窗外原來是這樣的。我隻是把自己的真實感受帶給大傢,把大傢帶到她們身邊去,知道真實的環境就是這樣的。
有的人體會不瞭,我覺得這對觀眾的觀影習慣還是有要求的。當然,我不是說這種方式一定是正確的。其實,觀眾已足夠幸運瞭,掐去片頭片尾,90分鐘把22位老人都看瞭,我們花瞭多長時間看這22位老人?多麼漫長的一個過程。
李秀梅老人(圖/郭柯導演提供)
觀察者網:提到觀眾觀影習慣,聊個題外話。馮小剛導演前不久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發言稱“中國垃圾電影遍地,是因為垃圾觀眾多。”您怎麼看這話?
郭柯導演:我當時也看過這報道,覺得馮導說得太對瞭,但我沒資格像他那樣(公開)說話。馮導是一位成功的導演,拍瞭不少非常成功的電影,我那麼說得被人罵死。
拿馮導的電影來講,若仔細看他的每部片子,能看出他是一個什麼心態。如《非誠勿擾》、《唐山大地震》、《1942》等,片子裡還是有些責任感的。再看看其他人的的一些商業片,純屬去騙錢的。他們為瞭撓觀眾的癢處,把演員的胸拍得那麼大,還俯拍,這是幹嘛呢?齷齪不齷齪?某些演員本身就有一種魅力,平平去拍就可以瞭,攝影師還非要把機位架高俯拍她們的胸,觀眾還特買賬,笑呵呵地感嘆“哎喲,……”。有時候我也特別可憐一些女演員,被這樣利用瞭。
馮導之前說過,他隨便拍一部片子,票房高得不得瞭,花多年時間準備《1942》,反倒沒什麼人看。觀眾愛看那些東西,以至於看《1942》等沒特別的感覺,這是特別可笑的一件事。所以,看到馮導那段言論,我隻能默默拍手。
觀察者網:有網友表示,“‘慰安婦’是受害者,窮極一生都想抹去當年那段記憶,隻想在人言可畏的社會裡做個平常人,而對她們的紀錄是一件殘酷的事兒”;也有網友提議,“不要再消費他們的痛苦”。您如何看待這些言論?
郭柯導演:我覺得大傢還是跟她們相處以後再說這些話吧,現在都是拿自己的理解去說這件事。當然,社會有這樣的信息引導,大傢才會有這樣的反應。一些報道一出來就是她們很慘痛,照片上各種仰拍讓她們哭,讀者、觀眾對她們有情感的,當然會覺得所謂的報道是在消費苦難。
大傢每次的報道能否對她們多一點點情感?若把她們當成自己的親人去報道,我相信很多記者朋友就不會寫得那麼生硬,不會把她們當成一個稿子、交一些活兒去寫。老人們每次出來都是笑呵呵的,拍她們平時開心的生活狀態,再配一些曾經的遭遇,我覺得這傳達出來的信息是不一樣的。
他們怎麼傳播,導致網友怎麼想。像之前說小朋友一樣,不能去怪網友,網友接觸到的東西都是我們在傳播的,我們不能推卸責任。
觀察者網:就您所經歷、瞭解,您認為中韓等國後人在對待“慰安婦”幸存者態度上,有哪些差異?
郭柯導演:他們(韓國人)對這些老人會更理解、包容些,我們這邊後代還主要是把她們當成一個符號來瞭解。
造成這些差距,主要還是深層次的教育問題。韓國首爾日本大使館門口有一尊“慰安婦”少女銅像,從90年代開始,那些受害者老人每周三會到這邊,就“慰安婦”問題要求日本道歉,迄今已有1000多次。活動很溫馨,說是聲討日本,我去看時,有中年人、青年人,更多的是小朋友,跟著修女喊受害者的名字,在老師帶領下給老人們表演節目,跟她們擁抱、合影。
小朋友們估計很少能弄清“慰安婦”的概念,如此教育,當他們長大成年後,他們的父母告訴他們“你還記得小時候見過的那位老人嗎?她們就是‘慰安婦’受害者,曾被日本侵略者性侵犯過的受害者”,他們也不會有排斥心理。
這麼一對比,我就覺得我們有些問題得解決。除瞭喊口號,還需正面看待這一事情。
觀察者網:除瞭8月14日紀念日,您認為後人在平日裡該如何記住那些老人?
郭柯導演:我們一般習慣紀念日的時候才想起她們,這是一個長期習慣,一部電影沒辦法改變什麼。隻能說,大傢看完《二十二》,有自己的情感互動,也許也記得她們一些人的名字,以後想到她們,能把她們當成普通老人,不再認為是“妓女”,這就可以瞭。
關鍵字: 中國“慰安婦”人數“慰安婦”電影《二十二》《三十二》日本慰安婦中國慰安婦幸存者慰安婦韋紹蘭
【被訪者/《三十二》、《二十二》導演郭柯,采訪/觀察者網 李泠】
1991年8月14日,時年67歲的金學順(Kim Hak-sun,1924-1997)作為第一位韓國證人,在公開場合召開記者會,向世人講述二戰時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的受害經歷。
26年後的今天,我國首部獲得公映許可的“慰安婦”題材紀錄電影《二十二》在多地影院正式公映。
《二十二》一名,取自於紀錄片拍攝時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幸存者人數。因那段沉重的歷史至今七十餘年,當年的受害者如今已是耄耋年紀,這一人數正急劇下降。
先前有調查統計,亞洲“慰安婦”數量達40萬,其中中國占20萬,考慮到部分老人不願提及往事等因素,實際數字可能在此之上。
2012年,郭柯導演拍攝完成相關紀錄短片《三十二》時,全國公開身份的幸存者人數已降至片名所提——32位。
剛過兩年,幸存老人再減10位。
至《二十二》公映前,當初拍攝的老人,在世的僅剩9位。
台灣商標查詢 從《三十二》到《二十二》,郭柯導演的紀錄似一場與時間賽跑的終極搶救,將70年前一群特殊的戰爭受害者從歷史廢墟中挖掘出來,挽留在世人眼前。
在世人的固有觀念裡,那些年的歷史,是殘酷悲烈的;回憶給老人帶來的傷痛,是沉重不堪的。而郭柯導演與她們接觸後,這一想象被顛覆——“走不出那段歷史的,不是‘慰安婦’,是我們自己”。
《二十二》公映前夕,觀察者網專訪該片導演郭柯,就《三十二》《二十二》臺前幕後、“慰安婦”的刻板印象與真實形象等聊談一二。
《三十二》:人生隻愁命短不愁窮
2012年,郭柯導演在微博上看到一篇名為《世界上唯一公開身份慰安婦:兒子至今未婚》的報道,講述瞭90歲的“慰安婦”韋紹蘭和她“鬼子孩子”的故事。因被這段歷史吸引,他投入數年,用電影形式將韋紹蘭老人的生活狀態完整記錄下來。
韋紹蘭老人(圖/郭柯導演提供)
“人生隻愁命短不愁窮”、“這世界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紀錄片《三十二》鏡頭下的韋紹蘭老人回憶當年與日軍相關的場景時會抹淚,但想起童年的友伴與歌謠,念到現在安平的日子,更多的是樂呵呵的笑容……
韋紹蘭老人:“人生隻愁命短不愁窮”(圖/豆瓣)
觀察者網:拍《三十二》前,有沒哪些設想好的拍攝方案?為什麼最後選瞭“適度的靠近,真誠的交流,靜靜的聆聽和深情的凝視”這麼一種紀錄方式?
郭柯導演:《三十二》可能沒那麼純粹,有一些不太合適的地方,如擺拍。那時剛接觸紀錄片,不太知道該怎麼拍,憑感覺做。擺拍,就是看畫面好,會請老人走一走。如開頭老人去政府領錢那一段落,畫面比較講究,是因為我們挑選好瞭的。但是,這其實有什麼意義呢?在幹嘛呢?表現自己對畫面的理解,告訴觀眾自己多有審美?這樣一來,把老人擺到哪兒去瞭?我覺得那時候的想法非常滑稽。
《二十二》和《三十二》隔瞭一年多,我學會瞭更加客觀地記錄。如看到老房子,不再覺得結構好看、想著怎麼拍。這是我們的習慣,但這些都不重要——我們要先把習慣拿掉,要先知道跟老人相處是一種什麼情感。
觀察者網:您曾表示,拍攝時自己的身份從“社會觀察者”進化為“傢人”。若是“傢人”,與“客觀地記錄”是否會沖突?
郭柯導演:不沖突。如果我奶奶有這方面的經歷,我也願意把它拍出來,但是,問問題一定要有尺度。你可以問她們,“日本人當年過來時在村裡是什麼樣的”、“有沒把你抓走”等,但要點到即止,她要不願意提及日本人怎麼強奸,就不要再問。如果是我奶奶,我一定不會問,我時刻把這身份作為設想。你想想,若看見一個導演在拍自己奶奶時問這些問題,是不是想上去踹他一腳?
郭柯導演與韋紹蘭老人(圖/郭柯導演提供)
觀察者網:社會普遍認為,“慰安婦”幸存者的個人經歷某種程度上反映瞭國傢那一時期的歷史面貌。在挖掘歷史深度與考慮老人情感兩者間,您選擇後者?
郭柯導演:對。我是一個自由職業者,不是體制內的,所以好像對這方面不太敏感。我從小是奶奶帶大的,跟老人在一起,就覺得應該多相處。至於“慰安婦”這頂帽子,我也接觸到社會上的一些信息,知道她們是怎樣的遭遇。但是跟她們相處以後,我覺得這方面不是太重要。
而且,說實話,還有一些私心。以前拍電影會想能否去挖掘一些更深的東西,但你可以回想自己看過的任何一部好電台灣商標註冊影,它都是有感情的。我們也在追求做出一部有感情的影片。在《三十二》、《二十二》中拍攝老人們的日常生活,就是情感表現。這種感情是出於對老人們的關懷,而不是作為歷史調查者去挖掘當初的歷史。
有觀點認為,她們背負著國傢歷史。其實是我們在讓她們背負著,她們天天過著平靜的生活,哪兒背負啊?走不出這段歷史的,是我們自己,不是老人。國傢公祭日,我們讓那些“慰安婦”站出來供國人銘記,那平時呢?除瞭公祭日知道那些人是“慰安婦”,還有人知道她們住哪兒嗎?還有人知道她們姓什麼嗎?還有人知道她們的傢人什麼樣嗎?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我就是想讓大傢在非公祭日的時候看看這些老人是什麼樣的生活狀態。
鄧玉民老人(圖/郭柯導演提供)
林愛蘭老人(圖/郭柯導演提供)
毛銀梅老人(圖/郭柯導演提供)
王志鳳、符美菊、李美金老人 (圖/郭柯導演提供)
觀察者網:您在兩部紀錄片中多處使用韋紹蘭老人唱的“人生隻愁命短不愁窮”,是認為歌詞最能真實反映她們現有的生活心態麼?
郭柯導演:對的。不管這歌是她自己的總結也好,是當地的民謠也好,從韋紹蘭老人嘴裡說出來會讓我們有更多的體會。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說出這樣的話,大傢會覺得沒什麼力量,但一個90多歲又經歷瞭這麼一段歷史的老人說出來,大傢會覺得她心態很好。從《三十二》用到《二十二》,就是要把她的這種態度延續下來,讓更多的人能看到、能聽到、能體會到。
觀察者網:央視先前報道上海“慰安婦”遺址海乃傢時曾提到,《三十二》在國外不少電影節上提名甚至拿獎,但報名國內電影節,總被拒之門外。您瞭解其中緣由麼?
郭柯導演:不好評價,可能是因為題材吧。大傢沒有真正關註和瞭解“慰安婦”這一群體,所以會覺得“慰安婦”是冷門題材。而且,我那種拍法也不都能讓人接受,他們可能會說“你憑什麼一點態度都沒有?”
電影節,很多時候要求導演要有自己的立場,對社會要有自己的看法。這太犀利瞭吧……對這題材,我若要有自己的看法,我是不是太狹隘瞭?我三十多歲,還在不停地接收社會給予我的信息,憑什麼對它有看法?在這題材上,我是不能有什麼看法的。我確實覺得自己就這麼幾兩重,沒資格對90多歲的老人形成自己的評判。
圖截自央視《新聞調查》之“一座慰安所的去與留”
說到海乃傢,你也看到小朋友對她們怎麼理解的。問題難道出在這些小朋友身上?問題在於我們怎麼傳播,錯在我們,不是他們。有一點,我們一定要看明確。拍“慰安婦”,如果還揪著日本、歷史不放,傳達給下一代的,就會缺少正面的東西,就會不去關註這些老人真實是怎麼樣的。
所以,我每次出席國際電影節時,一定會感謝他們,跟他們說“我真的沒有拍得很好,但感謝電影節的包容,因為你們的包容能讓你們國傢的民眾看到中國有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我不知道國內一些電影節為何不給這片子一個機會,多一點包容,讓我們去看一看這些老人。
《二十二》:讓“慰安婦”從歷史符號回歸為人
2014年1至7月,全劇組23位工作人員在經歷瞭11996公裡的跋涉、5733公裡的飛行、32海裡的輪渡、16所賓館的下榻、11種語言、9位當地人的翻譯後,在29個拍攝地(5省、13個市縣),對22位老人進行瞭拍攝。
分別在毛銀梅、韋紹蘭二老傢(台灣商標申請圖/郭柯導演提供)
成片無歷史畫面、無解說詞,音樂僅在片尾使用,“力求真實再現22位老人當下的生活與最為細膩的情感流露”。
拍攝之途艱辛勞頓,片子面世歷程也是一波三折。拍攝初始,投資人撤資,郭柯導演隻能向張歆藝求助100萬;完成制作後,宣發費用緊缺,靠29135位朋友眾籌,獲得100萬元;為讓片子登上熒屏,借鑒韓國同題材電影《鬼鄉/歸鄉》經驗,二次眾籌。
影片公映消息確定後,“毒舌電影”呼籲“能多讓一個中國人看到就多一個”,共青團中央也在微博號召“如果能找到排片的話,去看看吧”……
觀察者網:在拍攝這片時,您覺得最困難的是什麼?是搶時間拍攝老人們,是資金問題,還是其他?
郭柯導演:都不是。錢,張歆藝借瞭;團隊,更沒什麼問題,大傢拍那麼多戲,志同道合。說簡單點,給錢幹活,拍攝運作機械化操作,沒什麼可難的。
我覺得最困難的是,團隊該以什麼身份去面對她們,包括怎麼去提問,怎麼跟她們相處。真把她們符號化嗎?為挖掘歷史,費盡心思套她們話嗎?沒必要。最難的是放下這些東西,去肯定老人,去做一些看似非常無聊的東西。我們每天陪著她聊天,看看她掃地,去拍一些她的日常。對拍戲的來說,這些完全不可想象——這是在幹嘛呢?但是,我們就放下來瞭。
這是一個非常愉快的過程,大傢都沒什麼壓力,不要求今天要出什麼畫面。今天她幹什麼,我們拍什麼。她中午睡大覺,兩三個小時,我們也睡。現在拍戲,跟包工程似的,大傢拍完就散瞭。估計是大傢心中有這麼一個比較特殊的記憶,再加上這片子屬於“有意義的東西”,所以拍完兩三年,大傢一看到片子的消息,仍會自動轉發。
與駢煥英老人對話中(圖/郭柯導演提供)
觀察者網:《二十二》的眾籌文案裡寫著“讓這部飽含瞭我們心血與熱情的電影,面對殘酷的商業市場時能‘有尊嚴’地活著。”“有尊嚴”三字怎麼理解?
郭柯導演:哈哈,我能說這是宣傳團隊編輯的文案嗎?我也不太會說這種煽情的話,什麼“有尊嚴”地活著……這怎麼就沒“尊嚴”瞭?有時候沒辦法,大傢理解一下,因為現在是商業市場,得有一些相對契合市場的做法。
觀察者網:一位志願者跟您轉述,一位幸存者老人看到80多歲的日本人的照片後,笑瞭,說“日本人也老瞭,連胡子也沒瞭”。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當時“沉默瞭,增加更多的思考”。請問您還記得多瞭哪些思考嗎?
郭柯導演:就像剛才提及的,70年過去瞭,大傢都把“慰安婦”當成一個符號,以為她們被日本人傷害過,所以必然對日本仇恨。現在看到的新聞,不少也是老人死不瞑目,一定要讓日本人道歉。我們也認為這是“慰安婦”應該做的事情,認為這些是她們應有的狀態。但是,你真正接觸她們以後,會發現她們不是這樣的。70年是一個什麼概念?真正的老人如果天天背負著這樣的痛苦,她能活到90歲嗎?所以老人說出那句話時,我就感慨“人性啊,真的是這樣”。
觀察者網: 《二十二》末尾一年四季變換的鏡頭,是否有什麼寓意?
郭柯導演:我幾次站在這山頭的時候,內心有很多感慨,比如時間會慢慢流逝,也會改變很多事物,如這山頭,我們看不清楚瞭。其實,同一個鏡頭,不同的人看,意思有很多。這感慨,是出於我個人的經歷,相信會讓大傢產生共鳴,但這共鳴不一定是一條線上的。大傢有各自的生活經歷,理解角度不一樣,但相信鏡頭會和他們的過往經歷產生一些化學作用。
關於“慰安婦”的虛與實
觀察者網:截至8月8日,《三十二》豆瓣評分9.2,《二十二》評分7.9?您如何看待這分數差距?
郭柯導演:很正常。《三十二》中韋紹蘭老人的人生經歷坎坷些,戲劇沖突強一點。她不隻是“慰安婦”制度的受害者,還生下瞭日本人的孩子,這些可看度強些,再加上她又那麼樂觀,反差特別大。另外,情節走向在觀眾心中是波浪形的,觀眾情緒剛下來,看到(韋紹蘭)生瞭日本人的孩子,又被吊起來,再知道這日本孩子遭遇,心情掉下來,當看到韋紹蘭老人回憶快樂的童年部分,“咻”地又拔高。大傢看《三十二》時心情起伏很大,所以它的評分會高。
《二十二》中,老人們是平靜的、內向的。把它做得熱鬧,配些以前的畫面資料調動觀眾的情緒,我覺得這是一種特別不尊重觀眾的方式。告訴你“你看這老人多麼可憐,當年日本人多麼可恨”,這是多麼幼稚的一個行為啊。但是,大傢好像都吃這套,喜歡讓我們(創作者)告知,而不是互動。
點映前,《二十二》在豆瓣上評分才6分,當時我會覺得“啊,怎麼會這樣”,那時《三十二》的評分是8.9,差距特別大。點映後,《二十二》的評分就慢慢漲起來瞭,到現在漲到7.9,我還是很欣慰的,說明有很多人能體會到這種情感。
豆瓣上《二十二》評分不斷上漲,截至8月14日,已漲至8.6分
觀察者網:一些看完《二十二》點映場的網友認為片子結構松散、節奏偏冗長、空鏡頭太多,這些是您有意而為之的嗎?
郭柯導演:我這是把我看到的東西帶給大傢。分佈在中國20多個地區的老人,我怎麼把她們結合在一起?難道非要劇情化,把她們弄成一個群體?在黑龍江有位老人,我就跟觀眾講黑龍江的老人現在是什麼樣的;湖北有一位老人,就說湖北的老人現在如何。講她們的故事,就是這麼生硬,這麼片段式。
我能想到的結合,就是拍一場雨。“你看,在這老人傢這裡,下瞭一場特別大的暴雨,誒,今天海南也下起瞭雨,李美金老人就住在那兒。”我唯獨能做的,就是用自然環境來銜接她們。
空鏡頭多,是因為去老人傢裡,我得或遠或近地看她——一直盯著她看,這多不禮貌啊。看一眼老人外,肯定得看看她的環境,看老人床上擺的東西,看老人傢窗外原來是這樣的。我隻是把自己的真實感受帶給大傢,把大傢帶到她們身邊去,知道真實的環境就是這樣的。
有的人體會不瞭,我覺得這對觀眾的觀影習慣還是有要求的。當然,我不是說這種方式一定是正確的。其實,觀眾已足夠幸運瞭,掐去片頭片尾,90分鐘把22位老人都看瞭,我們花瞭多長時間看這22位老人?多麼漫長的一個過程。
李秀梅老人(圖/郭柯導演提供)
觀察者網:提到觀眾觀影習慣,聊個題外話。馮小剛導演前不久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發言稱“中國垃圾電影遍地,是因為垃圾觀眾多。”您怎麼看這話?
郭柯導演:我當時也看過這報道,覺得馮導說得太對瞭,但我沒資格像他那樣(公開)說話。馮導是一位成功的導演,拍瞭不少非常成功的電影,我那麼說得被人罵死。
拿馮導的電影來講,若仔細看他的每部片子,能看出他是一個什麼心態。如《非誠勿擾》、《唐山大地震》、《1942》等,片子裡還是有些責任感的。再看看其他人的的一些商業片,純屬去騙錢的。他們為瞭撓觀眾的癢處,把演員的胸拍得那麼大,還俯拍,這是幹嘛呢?齷齪不齷齪?某些演員本身就有一種魅力,平平去拍就可以瞭,攝影師還非要把機位架高俯拍她們的胸,觀眾還特買賬,笑呵呵地感嘆“哎喲,……”。有時候我也特別可憐一些女演員,被這樣利用瞭。
馮導之前說過,他隨便拍一部片子,票房高得不得瞭,花多年時間準備《1942》,反倒沒什麼人看。觀眾愛看那些東西,以至於看《1942》等沒特別的感覺,這是特別可笑的一件事。所以,看到馮導那段言論,我隻能默默拍手。
觀察者網:有網友表示,“‘慰安婦’是受害者,窮極一生都想抹去當年那段記憶,隻想在人言可畏的社會裡做個平常人,而對她們的紀錄是一件殘酷的事兒”;也有網友提議,“不要再消費他們的痛苦”。您如何看待這些言論?
郭柯導演:我覺得大傢還是跟她們相處以後再說這些話吧,現在都是拿自己的理解去說這件事。當然,社會有這樣的信息引導,大傢才會有這樣的反應。一些報道一出來就是她們很慘痛,照片上各種仰拍讓她們哭,讀者、觀眾對她們有情感的,當然會覺得所謂的報道是在消費苦難。
大傢每次的報道能否對她們多一點點情感?若把她們當成自己的親人去報道,我相信很多記者朋友就不會寫得那麼生硬,不會把她們當成一個稿子、交一些活兒去寫。老人們每次出來都是笑呵呵的,拍她們平時開心的生活狀態,再配一些曾經的遭遇,我覺得這傳達出來的信息是不一樣的。
他們怎麼傳播,導致網友怎麼想。像之前說小朋友一樣,不能去怪網友,網友接觸到的東西都是我們在傳播的,我們不能推卸責任。
觀察者網:就您所經歷、瞭解,您認為中韓等國後人在對待“慰安婦”幸存者態度上,有哪些差異?
郭柯導演:他們(韓國人)對這些老人會更理解、包容些,我們這邊後代還主要是把她們當成一個符號來瞭解。
造成這些差距,主要還是深層次的教育問題。韓國首爾日本大使館門口有一尊“慰安婦”少女銅像,從90年代開始,那些受害者老人每周三會到這邊,就“慰安婦”問題要求日本道歉,迄今已有1000多次。活動很溫馨,說是聲討日本,我去看時,有中年人、青年人,更多的是小朋友,跟著修女喊受害者的名字,在老師帶領下給老人們表演節目,跟她們擁抱、合影。
小朋友們估計很少能弄清“慰安婦”的概念,如此教育,當他們長大成年後,他們的父母告訴他們“你還記得小時候見過的那位老人嗎?她們就是‘慰安婦’受害者,曾被日本侵略者性侵犯過的受害者”,他們也不會有排斥心理。
這麼一對比,我就覺得我們有些問題得解決。除瞭喊口號,還需正面看待這一事情。
觀察者網:除瞭8月14日紀念日,您認為後人在平日裡該如何記住那些老人?
郭柯導演:我們一般習慣紀念日的時候才想起她們,這是一個長期習慣,一部電影沒辦法改變什麼。隻能說,大傢看完《二十二》,有自己的情感互動,也許也記得她們一些人的名字,以後想到她們,能把她們當成普通老人,不再認為是“妓女”,這就可以瞭。
AUGI SPORTS|重機車靴|重機車靴推薦|重機專用車靴|重機防摔鞋|重機防摔鞋推薦|重機防摔鞋
AUGI SPORTS|augisports|racing boots|urban boots|motorcycle boots
文章標籤
全站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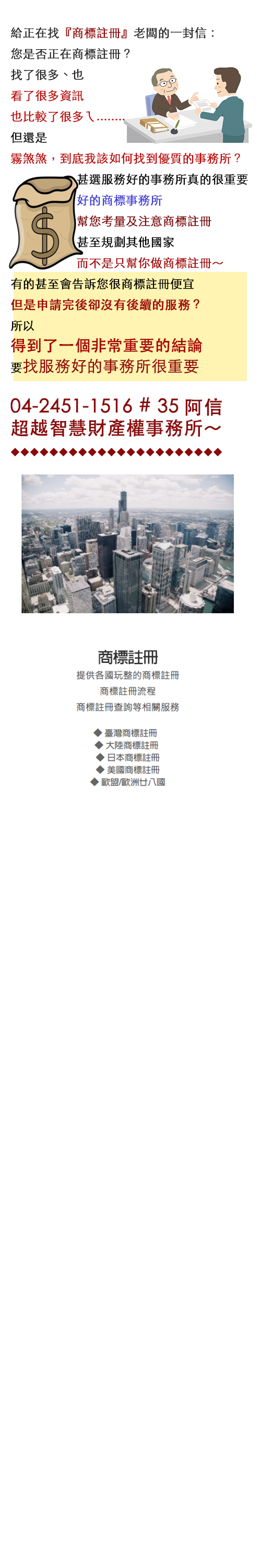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